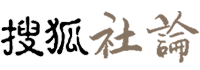指责“懒政”或“恶政”,在毒地风波前激荡心情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问题在于,常州外校的案例并不鲜见。关于全国毒地规模的准确数字从未有披露,它们随机分布,那就只能看它“抽中”哪个不幸的群体。
常州毒地风波,徒劳的愤怒等待中国式结局
常州外校紧邻有毒的化工用地,有学校家长报呈孩子出现与皮肤、甲状腺或淋巴有关的症状,怀疑它们与毒地污染高度正相关。媒体确立了“不安全感”作为报道方向,逐步叩击常州在毒地处理、规划及使用上的问题,所有悬疑汇聚,成为沸沸扬扬的毒地风波。
在这件事上,很容易就激发起来的愤怒,以及常州官方不甚高明的应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众抱持自身的生存体验,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安全感展现在常州毒地风波上。并且,一旦认识到不得不将安全感建设委托给政府,公众的不安全感愈加旺盛,此间郁结难解。
相较于大众交流无碍的不安全感,公众与政府的对话却显得晦涩、艰难。这缘于双方对事实的认定并不在一个层面。家长说毒地释放有毒空气,环保局说检测合格;媒体援引国际标准,部门只对国标负责。因为对事实不能有共识,真相只能是晦暗不明。
而媒体构建出来的真相,已经单兵突进。常州外校之所以迁建,有媒体暗示是常州为了腾出黄金地段搞房地产开发,毒地风波的因果关系陡然变成:政府放纵土地财政,学生健康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品。这种逻辑带有强烈的控诉性质,几乎是无可辩驳的。
僵局之下,所有人都在等待高等级的裁断。环保部已经派员进入常州,他们对毒地的处理及其成效性肩负着释疑解惑的责任。令人信服地解决毗邻毒地对包括常州外校在内的周边学校的困扰,目前只能等待上级的明镜高悬,家长及公众的选择并不多。
舆论中有讥讽常州外校的家长们“有钱也遭受践踏”、“不如早去移民”云云。可对当地中产家庭来说,入读常州外校是将子女送到国外的最优途径,因为该校教的深,教的快。就此,毒地风波的隐喻变成了:在逃离毒地之前,你愿意忍耐伤害到什么程度?
常州作为长三角中的经济洼地,经历了十多年的城市发展迷失,清查环保欠账,清算毒地风波,就不得不从常州的经济及发展挫折讲起——而往上追溯历史来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及思路,对解决常州外校引发的毒地风波既不够快速,也缺少圆满操作的可能。
前任遗留的毒地危害为何要本届政府承担责任?环保不力的后果为何要学校承受?学校比邻化工毒地的恶果为何要将学生卷入险境?毒地处理所需的科学技术及必需时间为何在标准前涣散?诸如此类的因果与错置像乱麻一样纠缠,再强烈的愤怒也会在国情前瓦解掉。
指责“懒政”或“恶政”,在毒地风波前激荡心情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问题在于,常州外校的案例并不鲜见。关于全国毒地规模的准确数字从未有披露,它们随机分布,那就只能看它“抽中”哪个不幸的群体。这也相当于为毒地风波从爆发到归于沉寂预设了中国式结局。
一句话来说,常州毒地风波展现了陈陈相因缺失与失灵,这些缺失与失灵分布在各处。而在诸如“全国八成地下水不能饮用”这些问题上,它们同样存在。无非是找到一块安全的立足之地,无非是喝上一口安全的水,愤怒在乍起与消停间折腾,叩问此伏彼起。
(搜狐评论独家原创,未经许可谢绝任何的形式的转载,申请转载请联系本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