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林海
2011年11月,陕西省略阳县。四名村镇干部酒后“睡”了一名12岁幼女。然而最终他们仅被认定为“嫖宿幼女”,其中刑期最重的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对此,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多意外。因为自从“嫖宿幼女罪”取代“与幼女发生性行为即构成强奸”的刑事规则近二十年来,大量性侵幼女的行径都被归入“嫖宿”这一看似无害的商业交易。
下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三审刑法修正案(九),有消息说,这次审议将可能会涉及“嫖宿幼女罪”。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早在将近十年前,我就听说过废除这项罪名的呼吁,在我看来,这一罪名早就该废除了。
这项罪名最讽刺的地方在于,获罪之人大多会感到“幸运”。因为强奸罪最高可致死刑,而嫖宿幼女罪最高则只会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加上在狱中或是“诚心改造”,或是“保外就医”,往往会被减刑或假释。当他们在庭受审时,心中多少也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商业交易”,没什么大不了。与此同时,那些被性侵的幼女,非但不会被视为受害者,反而被归入雏妓一类——这意味着她们非但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强奸的被害人获得赔偿,还将终生背上“自幼出卖肉体”的黑锅。
然而,这些未成年的孩子,有多少真正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为了金钱提供性服务?那些脑海中浮现日本援助交际的成年人,或许并不知道日本刑法第177条“与13岁以下幼女发生性行为视为强奸罪”的规定吧?我们看到,许多被性侵的幼女及其家长,要么迫于来自被告人(他们往往是强势的地方官员)直接的威逼利诱,要么担心社会舆论的压力对孩子未来成长造成二次伤害,宁愿息事宁人,而不愿出庭指证强奸;当法庭基于“事实”,适用刑法中关于嫖宿幼女的规定,最终仅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甚至更轻时,他们也不愿、不能或不敢再提起抗诉。
即便这些不满14岁的幼女真的是在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就可以宽宥那些面对幼女解开皮带的成年男性了吗?嫖宿一语,实际上在说明,这些幼女与成年嫖客之间,进行的是性“交易”。然而稍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完全的无行为能力人,他们既不能以自己名义进行商品交易,也不被允许被雇佣成为劳工,因为他们既不具备商品价值的识别能力,也不具备相应风险的承担能力。他们在商场尚且不能从事一台电冰箱、洗衣机的交易,又如何能成为性交易的一方呢?
这仿佛是在说,那些不被允许卖蔬菜、卖电器的幼女们,反而具备了卖淫所需要的自我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这样的逻辑难道还不够荒唐?试想,幼女们是不是真的都知道安全套的使用办法和重要意义?她们是否知道,无保护行为可能染上性病或是艾滋?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幼女们真的是自愿在出卖性服务吗?不到十四岁的孩子,真的知道这些“叔叔”是来干什么的吗?即使是对性服务业极为宽容的荷兰,也明确规定不允许低于13岁的女性提供性服务,因为她们还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世界各国的刑法中,对于儿童的性侵犯都会被处以极为严厉的惩罚。在韩国,有专门针对性侵幼女犯罪的化学阉割刑罚;在美国,一旦存在性侵儿童的犯罪纪录,将终身背上污点——犯罪人出狱后,搬到新的街区,社区工作人员有义务第一时间通知家长,保持对此人的警惕。这样对于儿童健康和其他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很难想象在某一泱泱大国、文明古国的刑法中,还会出现牺牲幼女、保护部分成年男性的条款。
从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强奸罪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暴力胁迫是强奸,以药迷奸也是强奸;最初同意卖淫,中途反悔被“霸王硬上弓”,也构成强奸。和不能作出清醒判断的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性行为,也一样视为强奸。我国刑法在出台嫖宿幼女罪之前,也坚持着这样的逻辑:与幼女和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性关系,即使对方同意,“你情我愿”,也一律视为强奸。那么,为什么十年前会进行刑法修改,制定关于“嫖宿”的罪名呢?
这是因为,对于一些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的成年男性来说,似乎确实难以辨别小姐的年龄。现实中即有这样的案例,几位局长在夜总会“消费”之后,老板微微一笑,拿出他们身下女子的身份证,以强奸罪名进行要挟。相似的情况多了,成年男性们便提出了修法诉求。然而,修法者在保护嫖娼的成年人们不受“陷害”时,似乎忘记了被“嫖宿”的幼女作为儿童和妇女的利益,在保护成年男性的“性自由”时,似乎忘记了这会给被害人贴上“卖淫女”的标签。这样以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为代价,去保护部分(往往是强势人群)的成年男性的立法,历经十年饱受争议而难以修改,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刑法学界和理论界的一件憾事。
我注意到,在这次刑法修改过程中,一审稿和二审稿都没有涉及到嫖宿幼女罪。但在审议过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学界人士纷纷发声,要求取消这一罪名,一律按强奸罪论处。真心希望,在本次三审过程中,立法者能够尊重舆论呼声,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不要再让我们的刑法中留有“嫖宿幼女罪”这样令男性汗颜、女性愤怒的字眼。
来源:团结湖参考微信公号 微信号:Talkpa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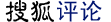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