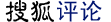 > 观察家
> 观察家 人参与)
人参与)我的故乡湖南新邵县,和新化、隆回两县交界处有羊古坳、观音山,此地在资江以西、雪峰山的东麓,山势险峻、绿树葱茏,千百年来成群的候鸟秋天经过这些地区,飞往南方去过冬,有“千年鸟道”之称。近日来,该地引起媒体关注,原因乃是两山这几年成为了猎杀者的游乐场和候鸟的屠场。
看到这一新闻,我想起了金朝大文豪元好问的《雁丘词》。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古往今来,人们吟诵它来歌唱矢志不渝的爱情。诗人有一段序述说了写这首词的背景:他去太原赴试途中,听一个猎人说捕杀了一只大雁,死雁的配偶已经脱网而飞,看到伴侣已死,它不愿独活,从空中触地自杀。元好问把这对大雁买下,埋在汾河边。
一对自由飞翔的大雁,在猎人的眼中是可以用来卖钱的猎物;在食客的眼中,是一顿美味;而在诗人的眼中,则是一对生死相依的爱侣。从元好问的这首词可看出,自古以来,猎杀鸟类的行为就存在。
人类为了生存,需要进行渔猎活动来获取食物,这在上古时期是不得已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一步步进入农耕和工商业社会,获取食物的途径日益广泛,生产食物的科技也日新月异,猎杀鸟兽已不是人类生存的不得已手段。当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生产技术依然无非和今天相比,在一些耕地较少的山区,打猎也长期成为人们食物的补充途径。如我的故乡——即新闻中所报道今天仍大量猎杀鸟类的新化、新邵一带,有一首歌男女之情的山歌,开头便如此比兴:“郎在对门高山打鸟嗨(耍的意思),姐在河边洗韭菜。”
但是,今天大肆猎杀候鸟和古代先民的猎杀其理由、情形已完全不同。首先,发达的农业和养殖业已经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丰富的食物,捕杀野鸟和野兽不是获取食物的必须;其次,古代由于人口密度小、猎杀鸟兽的技术低,而且猎人有种种避免“竭泽而渔”的禁忌,对鸟兽的生存影响是很小的,更不会让大自然的生物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而从新闻中可看出,今天湖南等地的猎鸟,成为一项产业,猎杀者使用的是现代化的装备,毫无禁忌地猎杀。
有购买则有杀戮,这是猎杀野生动物之风屡禁不止的原因。究竟是哪些人在消费被猎杀的鸟类?从媒体报道来看,主要是城市里的有钱人或部分地方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吃野鸟,和戴价格昂贵的手表一样,是一种炫耀性消费。
中国的饮食文化里,许多所谓的珍稀食品的价格,就是这种炫耀性消费人群在推波助澜。比如鱼翅,比如燕窝,比如那些被端上餐桌的野生动物,其营养价值并不比家养的鱼肉高,而且由于野生动物运动量大,肌肉纤维很粗,味道还不如家养的鲜美。然而,多数消费野生动物的人,获得的不是什么很特别的营养,吃的甚至也不是味道,而是某种并不科学的理念在支撑着这样的消费,即野味更补人。
如今,靠化学品催熟催肥的饲养肉品填塞着平民的肚皮,野味以天然肉的诱惑更让一些有钱人或有权人趋之若鹜,他们获得的其实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这种心理也可以说是“贪念”得到满足。这些人好食禁脔,通过获得平常人难以获得、甚至需要违法才能得到的东西,从而显示出自己不一般的社会地位,这就是“贪念”作祟。
当金钱和权力比翼双飞追逐禁脔时,单靠当地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效果很难奏效,很可能是媒体关注时轰轰烈烈搞一场运动式执法,风声一过一切照旧。要改变一些国人好食野味的陋习,从长远来看是要通过科学、法治教育来改变陈旧的饮食观念,做到“无购买则无杀戮”。而当下能做的,不仅仅是关注野生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而是要让权力运行透明,受到实实在在的制约和监督。当权力很难染指野生动物时,单纯用金钱来获取野生动物,必将承担昂贵的成本,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处罚才能不折不扣,而不是风乍起,仅仅“吹皱一池春水”。
范仲淹有词句 “衡阳雁去无留意”,典出大雁从北南飞,到湖南衡阳一带便不再南徙之说,至今衡阳尚有“回雁峰”。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真实的状况是:长途飞翔的大雁等候鸟在南岭以北的湖南衡阳、永州、邵阳一带山林里歇息,积蓄能量再继续往南。而人类的贪念,让这一带原本是鸟类的乐园,变成了鸟类的屠场。那么,猎杀者和消费者和古代猎人相比,除了猎杀器具的进步外,心理上是不是更趋于野蛮?
莫让“回雁峰”前再无雁。
相关评论:
而且猎杀候鸟还涉嫌枪支犯罪,一座山头有两三百伙人杀鸟,那么,就意味着有二三百条猎枪,到了这个季节罗霄山枪响不断,又有多少条枪?对于如此严重的涉枪犯罪,当地警方岂能袖手旁观?[详细](新京报)
一位专家出语惊人,当地一个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可能是一监守自盗的贼窝!他称,这个协会常常以合法的名义猎杀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以此获利,他还以亲身经历作证。[详细](南方报网)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