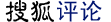 > 国际评论
> 国际评论 人参与)
人参与)香港《信报》7月14日文章,原题:如何避免南海“巴尔干化”
随着美国宣告“重返亚洲”之后,南海争端正向着复杂化、多边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的方向不断升级。虽然中国一直力求在“双边和纯主权争端”的框架内,把南海问题与多边的趋势隔离开来,但在美国已调整的全球战略下,上述的政治愿望已变得愈来愈不现实了。
面对南海局势愈来愈有可能转变成全球地缘争端的常态化中心,甚至成为亚洲的“巴尔干”,中国的战略界有必要未雨绸缪,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原有框架基础上,积极倡导“南海共赢新秩序”。
美国军费未来十年将缩减六千亿美元,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要继续保持全球的军事影响力,她必须找出可以借力补缺的杠杆战略,这已清晰体现在“Smart Power”的战略调整中。也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的被动性其实大于其主动性。
如果这一判断属实,可以说没有任何战略比“令南海争端常态化”更能确保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了。美国战略预算的公开化,客观上令南海小国和美国“重返亚洲”都成为了六千亿美元紧缩的补缺者和军事存在的体现者。
在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更合理的新秩序之前,美国国家利益必定与战争和军工密不可分,故此,即使千疮百孔,美国仍会维系美元在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中的“逆差型储备货币霸主地位”,以便借助国际能源(尤其是油气能源)在内的国际贸易体系,滋生出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之外的“美元政治”新维度。
换言之,南海争议的各方,实际上都不能摆脱“美元政治”新维度的政治操控。
“韬光养晦”应否继续
只要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或不能回归2004年之前每桶三十五美元左右的原有格局,南海的传统利益争夺就会发酵出远大于主权物理属性资源的倍增效应。
因为,当事各方都会因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而拥有更多的本钱,从而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源来参与南海博弈。
毋庸赘言,倘若没有1994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主权争端的理据——九段线的历史和属性依据不会如此复杂。如果承認《公約》,那么,南海當下的最大主導秩序就是《公約》。假设如此,就没有“南海争端”,只有“南海海洋法公约争端”。其实,“南海海洋法公约争端”只有三种结果:一、全盘否认《公约》,以求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最大化(因不允许保留,只能退出);二、在现有《公约》的框架内寻求争端的解决之道;三、部分超越现行《公约》,意在进一步完善《公约》,构建可进一步确保各方和整体利益的新体系,例如补充植入《南海共赢新秩序公约》,以求更有效解决南海争端。
像一切政治的本质一样,地缘政治首先是利益政治,其次才是权力政治,利益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共赢。当下所构建的中国地缘政治体系,存在诱使“南海争端常态化”的风险。中国地缘政治体系中不稳定的因素,必须给予及时的有效调整,否则,在大国博弈的背景下也有可能阴沟翻船。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出头、不称霸,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座右铭。埋头发展经济、专注国内事务的政治方略,似乎已被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佐证为金科玉律。
但“韬光养晦”和“政治不作为”之间缺乏“识别体系”,无法区别两者之间的差异;故此,“韬光养晦”实际上掩盖了中国缺乏“软实力”的事实。
中国过往三十年快速崛起背后的理论,如果不具可供他国借鉴的普遍性,就无疑不能产生影响力,也随之丧失话语体系。那麼,中國在處理地緣政治與國際政治議題時,又可以依據什么政治原則扮演角色?有鉴于此,中国有必要积极且全方位地开展“中国模式”的理论探索,以便在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与大国地位相称的领导者作用。
政治经济如何互补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以降,以主权为国家政治单位的国际体系,多是领导国所缔造的;没有领导国的存在,全球地缘政治秩序、现代国际政治秩序都荡然无存。想当大国,却又无力担当领导者的国家,无法在崛起道路上不与其他国家发生利益冲突;领导国实际上须要分配区内各国的政治利益,并化解纷争。
是与西方走过的发展道路一样,借助政治促进经济利益,还是借助经济利益来缓解政治矛盾和冲突;抑或是两者齐头并进相互促进,已经成为化解南海困局的一项重大战略议题。倘若没有新的政治框架安排或新秩序体系的出现,南海困局的可解性似乎渺茫大于希望。
在《公约》作为主导秩序的当下,南海争端的利益机制近乎纯粹零和型。即使作出重大的经济利益让步,也无益于扭转南海困局不断趋向“常态化”。毕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无限追求自己的政治梦想,但却可以无限追求自己的经济梦想。
所以,如何在零和型秩序框架下寻找出“共赢新秩序”,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恐怕已成为破解南海困局和可能的南海“巴尔干化”的最佳战略选择。
有鉴于此,南海争端是中国与当前国际社会“国际公约”之间的争端。所以,如何认清当前南海争端的战略,对中国的南海战略新判断而言,至关重要。在上述三点中,退出《公约》和框架内解决争端对美国最为有利,而建构“南海共赢新秩序”则对中国最有利。
(作者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特邀撰稿人、广东共赢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